这脑子疼得跟要炸开似的,耳朵边儿还嗡嗡响,吵死个人。陈山河猛吸一口气,一股子混着霉味、汗臭和铁锈的冷风直接灌进肺管子,呛得他一阵干咳,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“旗爷,旗爷您可算醒了!俺们还以为您这回挺不过去了……”一张黝黑枯瘦、胡子拉碴的脸凑到跟前,那眼神里的慌张和庆幸藏都藏不住。

陈山河没吭声,不是他架子大,是脑子彻底懵了。他眯着眼,看着头顶那几根结满蜘蛛网、黑黢黢的房梁,身下是硌得骨头生疼的破土炕,盖着的薄被子硬邦邦、潮乎乎的。刚才那汉子叫他啥?旗爷?啥旗?
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画面和念头,像开了闸的洪水,轰隆一下全冲进他脑子里。他,陈山河,一个在图书馆跟明史资料较劲的普通人,眼一闭一睁,嘿,直接干到大明崇祯年间来了!眼前这破地方,是辽东某个犄角旮旯的墩台,而他这具身体的原主,是个刚袭了爹职没多久的边军小旗,手底下管着十来号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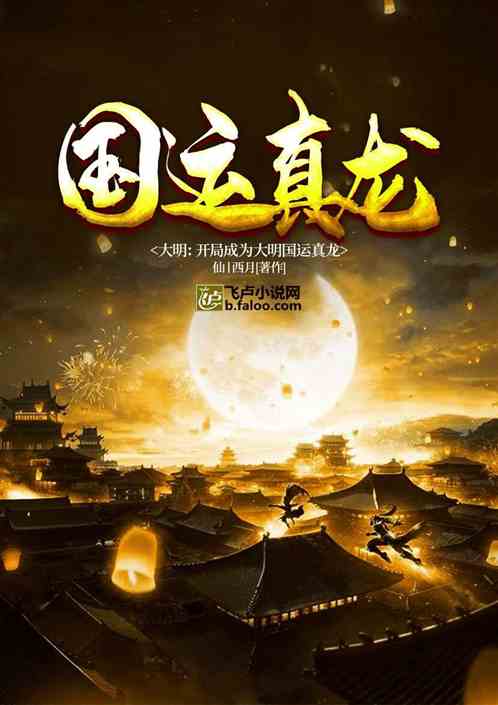
这开局,真是绝了!别人重生不是王爷就是少爷,他倒好,直接成了明末边军小旗。这可是明末啊,天灾人祸、鞑子叩边、流寇四起,朝廷穷得叮当响,当兵的连饭都吃不饱。他这小旗,说是个“官”,其实比大头兵也强不了多少,饷银层层克扣,到手里能买几斗糙米都算烧高香了。手底下这帮兄弟,一个个面黄肌瘦,身上的鸳鸯战袄补丁摞补丁,手里的兵器锈的锈、缺的缺-1-5。这烂摊子,想想都让人脑仁疼。
“水……”陈山河哑着嗓子挤出个字。
那黑脸汉子,也就是他手下叫赵墩子的,赶忙递过来一个豁了口的粗陶碗。水是凉的,带着股土腥味,陈山河却觉得从喉咙到肚子都舒坦了些。他靠着冰凉的土墙坐起身,慢慢打量这间所谓的“官房”。除了炕,就一张歪腿破桌子,墙角堆着些杂物,寒酸得不能再寒酸。唯一像点样的,可能就是挂在墙上那副旧皮甲和那把制式腰刀了。
“其他人呢?”陈山河问,声音还是有点虚。
“王驴子他们几个去巡墩了,李大眼在灶房那儿转悠,想看看还有没有能下锅的东西……”赵墩子搓着手,脸色有点尴尬,“旗爷,咱……咱墩里快断粮了。上次发的粮,本来就不多,还被上面……唉。”
话不用说全,陈山河也懂。层层盘剥,这是明末边军的常态-10。他这个重生明末边军小旗,睁开眼要面对的第一道坎,不是凶残的鞑子,而是手下兄弟空空如也的肚皮。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儿!
肚子饿,心里就慌,人心就散。想让这群面有菜色的汉子提起刀枪跟敌人拼命,先得让他们肚子里有食儿。这是最朴素的道理,也是陈山河眼下最头疼的难题。光靠那点微薄又不一定能及时到手的饷粮,根本活不下去。
歇了两天,身体稍稍恢复,陈山河就坐不住了。他穿上那身还算齐整的小旗号服,挎上腰刀,开始在墩台里外转悠。这墩台不大,就是个夯土垒起来的高台子,上面有瞭望的角楼,下面有几间土屋住人,围着矮墙-1。位置倒算险要,守着一片相对开阔的谷地。
他一边走,一边在心里盘算。前世那些零散的历史知识和杂学,这时候成了他唯一的指望。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,得自己想办法。
“旗爷,您看这……”赵墩子跟在他身后,欲言又止。
陈山河没回头,指着墩台后面一片长满荒草、乱石的空地问:“这地,能整出来不?”
“啊?”赵墩子一愣,“这地……土是薄了点,石头多,以前也没人正经种过。旗爷,您是想?”
“想活命,光指望上面发粮不行。”陈山河蹲下,抓了把土在手里搓了搓,“土是瘦,多拾点粪肥养养。石头多就捡出来,垒到边上。咱们人手不多,先开一小片试试,种点长得快、不挑地的菜。”
他自己心里也没十足把握,但必须试试。坐以待毙,不是他这个重生明末边军小旗该干的事。他记得好像有种叫“菠菜”的蔬菜,这个时候应该传进来了,或许能找到种子?就算没有,种点蔓菁、萝卜也行啊。
光种地周期太长,还得想点来钱(或来粮)快的法子。墩台靠近山区,他琢磨着能不能组织身手利索的兄弟,在不耽误值守的前提下,进山碰碰运气,打点野物改善伙食,皮毛攒起来或许还能换点东西。他甚至想起了以前看过的土法炼硝,不过这玩意儿有点敏感,得从长计议。
“墩子,”陈山河站起身,拍拍手上的土,“去,把咱们的人都叫过来,我有话说。”
不一会儿,包括巡墩回来的,一共十个人,稀稀拉拉地站在陈山河面前。一个个无精打采,眼里没什么光。陈山河看着他们,心里不是滋味。这些都是他的兵,也是他在这个乱世最初、最直接的依靠。
“兄弟们,”陈山河清了清嗓子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有力些,“日子难,我知道。饷粮指望不上,我也知道。但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熬着,把自己饿死在这墩台里!”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一张张木然或疑惑的脸:“从明天起,咱们除了轮值守墩,还得干点别的。身体好些的,跟我去后山把那片荒地拾掇出来,咱们自己种点吃的!手脚灵便的,轮流跟我进山转转,弄点野味给大家开开荤!咱们自己救自己!”
底下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,大多是不信和茫然。自己种地?当兵的种地?听着就不靠谱。
陈山河知道空口白话没用,他提高声音:“我,陈山河,既然做了这个重生明末边军小旗,带着你们在这鬼地方,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挨饿等死!出了力,种出来的粮、打到的猎物,按出力多少分!我陈山河要是多吃多占,天打雷劈!”
也许是他的眼神够狠,也许是那句“自己救自己”戳中了大家心里最深的恐惧和渴望,议论声渐渐小了。赵墩子第一个站出来:“旗爷,俺跟您干!总比饿死强!”
有人带头,慢慢地,其他人也犹犹豫豫地应和起来。改变,就从这片荒地和周围的大山开始。陈山河知道,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他这个重生明末边军小旗,要做的不仅是填饱肚子,还要把这些散漫惯了、对未来绝望的边卒,重新捏合成一支有点模样的队伍。后面要操练,要搞装备,要应对可能的敌情,难事儿多着呢。但饭得一口一口吃,路得一步一步走。活下去,才有资格想别的。